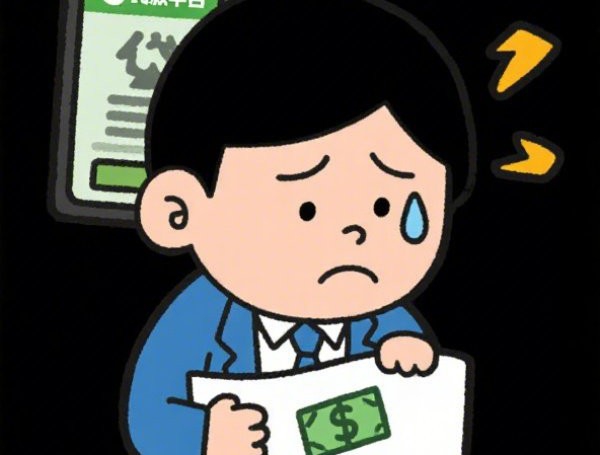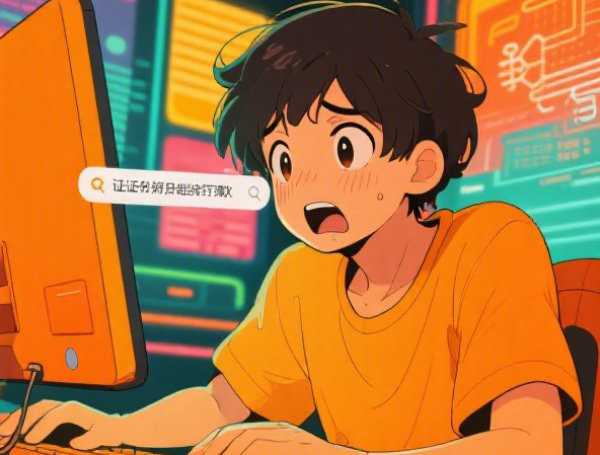香港某公司贷款合同案:违约风险、法律解析与应对
凌晨两点,中环云咸街那间24小时营业的茶餐厅里,我把一叠发黄的文件摊在桌面,同桌的师兄——做了二十年跨境融资的老律师——终于开口:“你手里的香港某公司贷款合同案,其实比新闻里写的还要曲折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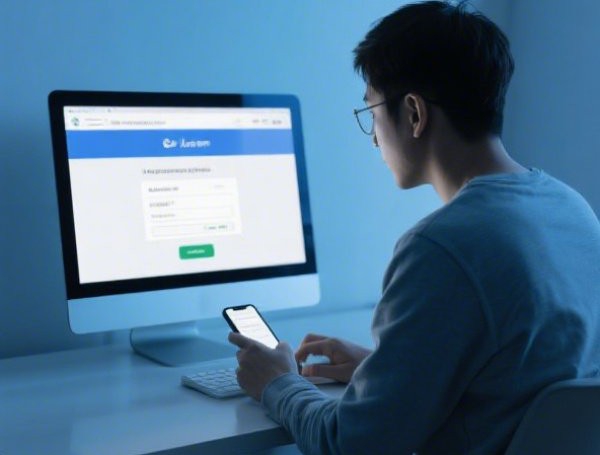
故事得从2019 年说起。一家总部在香港、业务遍及东南亚的物流集团,为了抢下越南港口的扩建标,急需 3.8 亿美元过桥贷款。他们在短短两周内敲定了与某欧资行的合同,却因为一条看似“无伤大雅”的条款,把整家公司推到悬崖边。条款原文只有 37 个英文字:“Any material adverse change in the Borrower’s consolidated financial condition shall constitute an immediate event of default.” 中文大意是:只要借款人整体财务状况出现重大不利变化,贷款立即到期。乍看只是行规,可真正的雷埋在“material adverse change”这五个字里——没有量化标准,解释权完全归银行。
疫情爆发后,空运量腰斩,该公司 2020 年一季度 EBITDA 暴跌 62%。欧资行随即援引上述条款,要求 30 天内全额清偿。公司高层连夜飞往香港,试图以“疫情属不可抗力”谈判展期,却被告知:合同适用英国法,而英国高等法院 2016 年已有判例,传染病流行并不自动构成不可抗力。换言之,香港某公司贷款合同案的核心争议,并不是“钱还不还得起”,而是“触发违约的那句话到底该怎么读”。
我翻阅内部邮件,发现欧资行在签约前三个月就悄悄把“material adverse change”从“reasonably expected to have”改成了“in the sole judgment of the Lender”——单看字面,只是多了几个词,却把客观标准改成了银行主观判断。更棘手的是,当时公司 CFO 正在医院陪护早产的儿子,文件由副手代签,副手只核对金额、利率,没留意这一处微调。等到争议爆发,这份扫描件成了银行手里的王牌。
接下来的 14 个月里,案件一路从香港高等法院打到英国商事法庭,光律师费就烧掉 4700 万港币。最终双方在伦敦秘密和解:公司让渡越南港口项目 18% 股权,银行放弃追索 1.2 亿美元违约金。新闻稿里只有一句“双方对结果表示满意”,可我在师兄的旧文件夹里,找到了和解协议副本——在密密麻麻的保密条款之后,有一行小字:若未来五年内该公司再融资,欧资行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承贷权。也就是说,这家香港公司哪怕东山再起,也依然被这笔贷款合同案的长尾条款牢牢套住。
师兄把杯里的冻柠茶一饮而尽,声音低了下来:“做融资的人常说,合同是最后一块遮羞布。可当风暴来了,谁先撕布谁就赢。”他把文件推回给我,“写报道时别只盯着数字,让读者记住‘material adverse change’这句话,下次他们自己签贷款,起码知道要在旁边加一句:‘以双方认可的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书面意见为准’。”
走出茶餐厅,天已微亮,皇后大道中的双层巴士缓缓驶过。我忽然想起那位 CFO 在败诉后发给全公司的一封内部信,信末只有八个字:“条款无声,却最锋利。”这句话,或许才是香港某公司贷款合同案留给所有创业者最昂贵的教训。